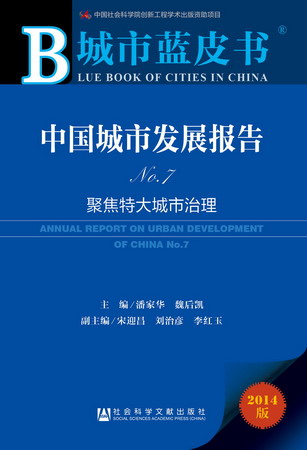专家视点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规模扩张。1978 年,中国没有千万人口级别的巨型城市,2010 年第6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已有6 个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其中城区千万人口以上的有2 个; 1978 年全国只有29 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 2010 年则达到140 个 。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挑战加剧, 显示出明确划定特大城市边界 、提升特大城市的治理能力的时代意义。
何谓特大?衡量一个城市的规模或水平,有许多指标。从行政级别上,有省级、副省级、地级(个别为副地级)、县级,有人甚至提出副县级城市。从政治地位上看,有首都、普通直辖市、省会、省辖市、地区及县行政所在地。尽管有地级以上城市的统计,但并不表明地级城市就是特大城市,甚至也可能不是大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和自然资源承载水平等自然属性指标也不是关键指标。尽管经济总量显示发展水平和市场引领能力,但城市规模的核心—尽管不是唯一指标—显然是人口数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按城区人口数量分为7 个级别:千万以上, 500 万-1000 万,300 万-500 万,100 万-300 万, 50 万-100 万,50 万以下以及镇。按照市民化要求户籍放开程度,建制镇和小城市即50 万人口以下的市镇全面放开;50 万-500 万人口城市分别为有序放开、合理放开、合理确定落户条件;5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则严格控制。因而,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区人口规模100 万-500 万为大城市,500 万以上为特大城市。从世界范围看,百万人口规模无疑是特大城市; 但在中国则多达140 个,似乎标准有些宽松。但事实上,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已经不是一般的大,因而本报告将特大城市标准定在100 万, 显然是客观的,具有世界可比性的。
城市发展有边界吗?经济发展的边界外延是市场竞争的张力所致。显然,这不是我们要控制的边界。城市各种功能的发挥,必然需要一定的空间,因而,城市功能如商务、文化、制造、教育、居住、休闲等功能拓展,意味着城市空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但是,一些城市功能如制造、教育并不必然要求集聚,可以分散或疏解;因而,功能并不能成为规模不可控或突破边界的理由。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也有规模负效益,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城市交通拥堵,交通时间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更加稀缺,供给成本增加,环境污染加重,环境成本增加,这些成本不仅会抵消规模效益,还会有负效益。这就意味着,从经济视角看,特大城市应该有边界,就是规模扩张的边际收益等于零。在城市辖区范围内,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一定的,例如土地面积、水源、蔬菜以及能源等,不可能是无限的,有着自然的边界。当然,规模负效益和环境约束均可被技术进步所舒缓。例如,地上高楼营造和地下空间利用, 可以缓解土地约束压力,快捷交通技术可以疏解交通拥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宜居环境可能不需要这种技术的无限发展和利用,而且,技术也不可能是没有成本的,例如高楼需要能源运行电梯,地下空间需要能源提供人工光源。因而,特大城市可以有边界,而且应该有边界。
谁来划定特大城市边界?计划经济体制下, “万能”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城市边界,现有的城市空间满足不了城市功能的需要, 则通过征地兼并临近地段的村、镇、县的方式摊大饼扩展城市空间和人口边界;环境容量约束也是通过行政手段,例如限制上游地区用水, 甚至远距离调水,以保障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边界扩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为了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说“功不可没”。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超出了城市就业岗位数,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市人口规模。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城市人口规模边界的管控方式, 可以用来划定并控制特大城市的边界吗?靠行政权力运作的功能需要边界扩充的摊大饼方式, 只能是“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特大城市的边界不可能得到有效管控。过去的经验表明, 拓展功能划定新开发区、产业园区,然后再吸引各类人员入驻。实际上,以行政命令调用外地资源与环境容量来满足特大城市的边界扩张, 不仅是一个不公平问题,更是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不利于城市健康发展。户籍歧视和强制“上山下乡”,不仅是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侵害, 也是社会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妨碍公平竞争, 使要素资源不能在市场上得到有效配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加强社会治理,提升治理能力,特大城市的边界划定与管控,必须要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城市治理,不光是政府的事,也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包括市民、企业、社团等。与其他城市或周边地区的关系,也是一种公平参与式的治理,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令管制。例如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是北京作为强势的首都地位强行要求河北保北京,而是协同控制,这就是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参与式的治理构架的一种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社会各方遵循的法制环境和生态环境。强势政府的城市管理, 政府的条例就是法律;城市治理,则要求政府从立法执法的多重身份中解脱出来,在法律授权下行驶有限权力,例如城市规划,市长或政府不可随意修编,市民、社会团体也有发言权。生态环境是一种刚性约束,参与城市治理的各方,必须认识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这就要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尤其是城市治理构架中各方的科学认知和法制规范的能力。这样,法律和经济手段就成为特大城市边界划定并管控的有效手段,城市规划不可随意调,生态红线不宜贸然破。特大城市各种服务、资源供给和社会保障的成本费用就是一个门槛。纽约曼哈顿的高额停车费,使私家车出行者望而却步; 高昂的房价、水价、电价必然要排斥低效的产业和低收入人群。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没有户籍管理,城市的人口规模边界依然管控有效。
本文摘自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
主编/ 潘家华 魏后凯
副主编/ 宋迎昌 刘治彦 李红玉
978-7-5097-6433-6 / 2014 年 9 月/ 69.00 元